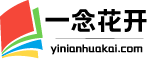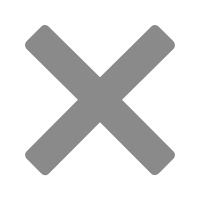-
做自己的光
第4章
当晚,我起了高烧,昏昏沉沉间,我做了个梦。
梦里有一个人的身影,模糊的看不清样子,只能勉强辨认出那个人身上穿的衣服颜色。
“你……来看我了。”
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也迈不开步子,好像有什么强力胶水把我粘牢在原地一样,动弹不得。
梦里,面对那个人,我很放松,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快。
我没有听到那个人说话,奇怪的是,我好想知道会说什么一般,脑海中自动浮现出一句话,“又被欺负了?”
“没有,”我摇头,落在那人身上的视线再一次被一层水雾模糊,“我就想见见你。”
我想你了。
这是一个无厘头的梦。
准确的说,是我心底隐藏已久的过去。
我睁开眼,黑白色调的装饰落进我的眼里。
昨晚的表现取悦了他,祁伯臣没有再将我丢到地下室。
身上阵阵钻心噬骨的疼,我恍若未觉,赤着脚下地。
卧室的空间很大,暗色大理石纹理地板明净透亮,干净的能照出人的样子。
祁伯臣向来注重体面,昨晚的事情,他不会让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个人知道。
他从来不会把自己隐秘又变态的想法暴露在大众的面前。
就连在我身上留下的伤,都是他亲手涂的药。
我弯腿,拿过被扔在一旁的衣服披上,遮住破败不堪的身躯,推门出去。
祁伯臣无声无息的站在门外,金丝框眼镜遮盖住一双阴鸷又锐利的眸。
斯文败类,衣冠禽兽。
我被他吓的后退了几步,冰凉凉的地面大方的向我传递它的温度,自脚底蔓延,浸入四肢百骸。
“你……你回来了……”
“沉沉,”祁伯臣唤的亲昵又阴冷,“要去哪?”
“我想回公司。”
我如实回答。
“首映结束后,网上有很多不好的言论,我……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我仰头,把自己摆在最弱势的位置,开口。
祁伯臣脸色好看了几分。
他享受被弱者仰望的感觉。
如同高高在上的神明,接受凡人的供奉。
“沉沉,我不喜欢不听话的宠物。”
阴恻恻,甜腻腻的声音让我作呕。
他在敲打我,让我注意。
“我知道,”在他身边待了一年,什么样的姿态姿态最能取悦他,我早就已经摸透,“处理完,我就回来。”